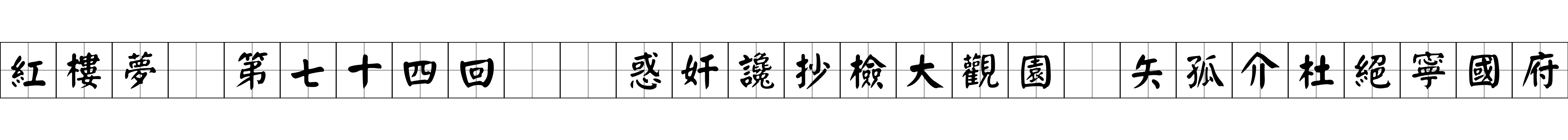紅樓夢-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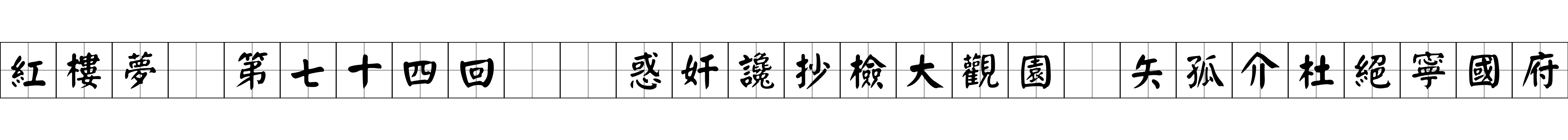
紅樓夢以錯綜複雜的清代上層貴族社會爲背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爲主線,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榮衰的描寫,展示了18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可謂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
話說平兒聽迎春之言,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她和她妹子是夥計,雖然她妹子出名,其實賺了錢,兩個人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因得此信,便慌了手腳,因思素與怡紅院人最爲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等人。金星玻璃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討情,比自己獨去,單爲柳家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你的病可好了?跑來作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閒話。
平兒便出去辦累絲金鳳一事。那王住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去就過去了。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去贖了來,交與我送去,我一字不提。”王住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我趕晚拿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
平兒到房,鳳姐問她:“三姑娘叫你作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着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喫些什麼。”鳳姐笑道:“倒是她還記掛着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她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爲,都是她作主。我想,況且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就可閒一時心,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些,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自己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得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病好了,我也作個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白不在我心上。”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便是我們的造化。”
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纔剛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裏先遷挪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日節間使用。我回沒處遷挪。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遷挪,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說沒地方?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哪裏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子二百銀子,你就這樣。幸虧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一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一個外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也可巧來送漿洗衣服。她在下房裏坐了一會子,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小丫頭們不知道,說了出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來?衆小丫頭慌了,都跪下賭咒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多說。“鳳姐詳情說:”她們必不敢,倒別委屈了她們。如今且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咱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來,且去暫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索性多押二百,咱們也要使呢。“鳳姐道:”很不必,我沒處使錢。這一去還不知指哪一項贖呢!“平兒拿去,吩咐一個人喚了旺兒媳婦來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
這裏鳳姐和平兒猜疑,終是誰人走的風聲,竟擬不出人來。鳳姐又道:“知道這事還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生出別的事來。打緊那邊正和鴛鴦結有仇了,如今聽得她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那起小人眼饞肚飽,連沒縫兒的雞蛋還要下蛆呢,如今有了這個因由,恐怕又造出些沒天理的話來,也定不得。在你璉二爺還無妨,只是鴛鴦正經女兒,帶累了她受屈,豈不是咱們的過失!”平兒笑道:“這也無妨。鴛鴦借東西看的是奶奶,並不爲的是二爺。一則鴛鴦雖應名是她私情,其實她是回過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孫男弟女多,這個也借,那個也要,到跟前撒個嬌兒,和誰要去?因此只裝不知道。縱鬧了出來,究竟那也無礙。”鳳姐兒道:“理雖如此。只是你我是知道的,那不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呢!”
一語未了,人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爲何事親來,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己的小丫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裏間坐下。鳳姐忙奉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裏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光景,心內着慌不知怎麼樣了,忙應了一聲,帶着衆小丫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索性將房門掩了,自己坐在臺磯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
鳳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內擲出一個香袋子來,說:“你瞧!”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哪裏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哪裏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裏,拿你當個細心人,所以我才偷個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的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裏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着,不虧你婆婆遇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遺在那裏來?”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說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再女孩子們是從哪裏得來?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哪裏弄來。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玩意兒,年輕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丫頭們揀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揀着,拿出去說是園內揀着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
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漲了麪皮,便依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得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的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詳其理:那香袋是外頭僱工仿着內工繡的,帶子、穗子一概是市賣貨。我便年輕不尊重些,也不要這勞什子,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一。二者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縱有,也只好在家裏,焉肯帶在身上,各處去?況且又在園裏去,個個姊妹,我們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我就年輕不尊重,亦不能胡塗至此。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算起奴才來,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人了。況且她們也常進園,晚間各人家去,焉知不是她們身上的?四則除我常在園裏之外,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如嫣紅、翠雲等人,皆系年輕侍妾,她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她不算甚老外,她也常帶過佩鳳等人來,又焉知不是她們的?五則園內丫頭太多,保得住個個都是正經的不成?也有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着出去,或藉着因由,同二門上小幺兒們打牙犯嘴,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
王夫人聽了這一席話,大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過我氣急了,拿了話激你。但如今卻怎麼處?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說是前日從傻大姐手裏得的,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衆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才得確實,縱然訪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這叫作‘胳膊折在袖內’。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裏,以查賭爲由。再如今各處的丫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事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沒有別的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也甚可憐了。也不用遠比,只說你如今林妹妹的母親,未出閣時,是何等的嬌生慣養,是何等的金尊玉貴,那纔像個千金小姐的體統。如今這幾個姊妹,不過比人家的丫頭略強些罷了。通共每人只有兩三個丫頭像個人樣,餘者縱有四五個小丫頭子,竟是廟裏的小鬼。如今還要裁革了去,不但於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富貴,比你們是強的。如今我寧可省些,別委屈了她們。以後要省儉,先從我來倒使得。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她們快快暗地訪拿這事要緊。”鳳姐聽了,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
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餘者皆在南方各有執事。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方纔正是她送香囊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她來打聽此事,十分關切,便向她說:“你去回了太太,你也進園內照管照管,不比別人又強些?”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鬟們不大趨奉她,她心裏大不自在,要尋她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這事來,以爲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託她,正撞在心坎上,說:“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早嚴緊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裏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她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的丫頭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擔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是個常情,跟姑娘的丫頭,原比別的嬌貴些。你們該勸她們。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導,尚且不堪,何況她們。”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都還罷了。太太不知道,頭一個寶玉屋裏的晴雯,那丫頭仗着她生得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得像個西施的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她就立起兩個騷眼睛來罵人,妖妖嬌嬌,大不成個體統。”
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裏罵小丫頭。我的心裏很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檻兒,這丫頭想必就是她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她原有些輕薄。方纔太太說的倒很像她,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她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房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笨笨的倒好。若有這個,她自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況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頭來,吩咐她到園裏去,“只說我說有話問她們,留下襲人、麝月服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她即刻快來。你不許和她說什麼。”
小丫頭子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她來。素日這些丫鬟皆知王夫人最嫌嬌妝豔飾語薄言輕者,故晴雯不敢出頭。今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妝飾,自爲無礙。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她釵嚲鬢鬆,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遺風,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個美人!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乾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
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她本是個聰明過頂的人,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對,只說:“我不大到寶玉房裏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道,只問襲人、麝月兩個。”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作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裏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裏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笨,不能服侍。老太太罵了我,說‘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麼!’我聽了這話纔去的。不過十天半個月之內,寶玉悶了,大家玩一會子,就散了。至於寶玉飲食起坐,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又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閒着還要作老太太屋裏的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
王夫人信以爲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她幾日,不許她在寶玉房裏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她。”喝聲“去!站在這裏,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妝扮!”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帕子捂着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門內去。
這裏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養息身體要緊,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主兒也極容易,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她們個猛不防,帶着人到各處丫頭們房裏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隻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東西。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她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太說得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定。
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善保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併入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屋內抄檢起,不過抄檢出些多餘攢下蠟燭、燈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贓,不許動,等明兒回過太太再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爲何,直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丫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說,一面坐下喫茶。
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知道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檢,只得自己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檢一番,不過是平常動用之物。遂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了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不開了讓搜?”襲人等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豁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朝天,往地下盡情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往別處去。鳳姐兒道:“你們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衆人都道:“都細翻看了,沒有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對象,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沒甚關係的。”鳳姐聽了,笑道:“既如此,咱們就走,再瞧別處去。”
說着,一徑出來,因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檢只抄檢咱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裏,斷乎檢抄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了,忽報這些人來,也不知爲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她不許起來,只說:“睡着罷,我們就走。”這邊且說些閒話。
那個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丫鬟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檢了一番。因從紫鵑房中抄出兩副寶玉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披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年往日手內曾拿過的。王善保家的自爲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哪裏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她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這也不算什麼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里的帳也算不清。要問這個,連我也忘了是哪年月日有的了。”王善保家的聽鳳姐如此說,也只得罷了。
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遂命衆丫鬟秉燭開門而待。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索性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淨她們的好法子。”探春冷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她們所有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頭們把箱櫃一齊打開,將鏡奩、妝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我。何必生氣。”因命丫鬟們快快關上。
平兒、豐兒等忙着替待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卻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裏間收着,一針一線,她們也沒的收藏,要搜,只管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己家裏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說着,不覺流下淚來。
鳳姐只看着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裏,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細的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裏,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護着丫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查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翻明白了。”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她自爲衆人沒眼力,沒膽量罷了,哪裏一個姑娘家就這樣起來,況且又是庶出,她敢怎麼!她自恃是邢夫人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況別個。今見探春如此,她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與她們無干。她便要趁勢作臉獻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鳳姐見她這樣,忙說:“媽媽走罷,別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聽“拍”的一聲,王善保家的臉上早着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善保家的問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專管生事。如今發了不得了。你打量我是同你們姑娘那樣好性兒,由着你們欺負她,你可就錯了主意!你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說着,便親自解衣卸裙,拉着鳳姐說:“你細細的翻,省得叫奴才來翻我身上。”鳳姐、平兒等忙與探春束裙整袂,口內喝着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喫兩口酒,就瘋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太也衝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勸探春休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性,早一頭碰死了!不然豈許奴才來我身上翻賊贓呢。明兒一早,我先回過老太太、太太,然後過去給大娘陪禮,該怎麼,我就領。”
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個沒意思,在窗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捱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孃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它做什麼!”探春喝命丫鬟道:“你們聽着她說話,還等我和她對嘴去不成?”待書等聽說,便出去說道:“你果然回老孃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捨不得去!”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作賊的人,嘴裏都有三言兩語的。這還算笨的,背地裏就只不會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勸,一面又拉了待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服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暖香塢來。
彼時李紈猶病在牀上,她與惜春是緊鄰,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才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丫鬟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麼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得不知當有什麼事故鳳姐也少不得安慰她。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金銀錁子來,約共三四十個;又有一副玉帶板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入畫也黃了臉。因問:“是哪裏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只要喫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
惜春膽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你要打她,好歹帶她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這話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什麼不可以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着哭道:“我不敢扯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她這次方可。這裏人多,若不拿一個人作法,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樣呢。嫂子若饒她,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她還好。誰沒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犯下,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後門上的張媽。她常肯和這些丫頭們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她。”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於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來。
迎春已經睡着了,丫鬟們也纔要睡,衆人叩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丫鬟們房裏來。因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孫女兒,鳳姐倒要看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她搜檢。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要蓋箱時,周瑞家的道:“且住,這是什麼?”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錦帶襪並一雙緞鞋來。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裏面有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與鳳姐。鳳姐因當家理事,每每看開帖並賬目,也頗識得幾個字了。便看那帖子是大紅雙喜箋帖,上面寫道:
“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覺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之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託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得說話。千萬,千萬!再所賜香袋二個,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
鳳姐看罷,不怒而反樂,別人並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她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又看着笑,她便說道:“必是她們胡寫的賬目,不成個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帳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孃,她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勉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她表弟。”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唸了一遍,大家都嚇一跳。這王善保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她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又都問着她道:“你老可聽見了?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如今據你老人家,該怎麼樣?”
這王家的只恨沒地縫兒鑽進去。鳳姐只瞅着她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笑道:“這倒也好。不用你們老孃操一點兒心,她鴉雀不聞的給你們弄個好女婿來,大家倒省心。”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善保家的氣無處泄,便自己回手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在人眼裏。”衆人見這般,俱笑個不住,又半勸半諷的。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深,且不必盤問,只怕她夜間自愧去尋拙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起她來。帶了人,拿了贓證回來,且自安歇,等待明日料理。
誰知到夜裏又連起來幾次,下面淋血不止。至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發暈,遂撐不住。請太醫來,診脈畢,遂立藥案雲:“看得少奶奶繫心氣不足,虛火乘脾,皆由憂勞所傷,以致嗜臥好眠,胃虛土弱,不思飲食。今聊用昇陽養榮之劑。”寫畢,遂開了幾樣藥名,不過是人蔘、當歸、黃芪等類之劑。一時退去,有老嬤嬤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等事暫且不理。
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到園中去又看過李紈。纔要望候衆姊妹們去,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遂到了她房中來。惜春便將昨晚之事細細告訴與尤氏,又命將入畫的東西一概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她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竟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胡塗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丫頭這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我立逼着鳳姐姐帶了她去,她只不肯。我想,她原是那邊的人,鳳姐姐不帶她去,也原有理。我今日正要送過去,嫂子來得恰好,快帶了她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入畫聽說,又跪下哭求,說:“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從小兒的情常,好歹生死在一處罷!”尤氏和奶孃等人也都十分分解,說:“她不過一時胡塗了,下次再不敢的。她從小兒服侍你一場,到底留着她爲是。”
誰知惜春雖然年幼,卻天生成一種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獨僻性,任人怎說,她只以爲丟了她的體面,咬定牙,斷乎不肯。更又說得好:“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我每每風聞得有人背地裏議論什麼,多少不堪的閒話!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排上了。”尤氏道:“誰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還有一句話:我不怕你惱,好歹自有公論,又何必去問人。古人說得好,‘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知道保得住自己就夠了,不管你們。從此以後,你們有事別累我。”
尤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人都說這四丫頭年輕胡塗,我只不信。你們聽方纔一篇話,無原無故,又不知好歹,又沒個輕重。雖然是小孩子的話,卻又能寒人的心。”衆嬤嬤笑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要喫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卻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幾個字,所以都是些呆子,看着明白人,倒說我年輕胡塗。”尤氏道:“你是狀元、榜眼、探花,古今第一個才子。我們是胡塗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狀元、榜眼難道就沒有胡塗的不成?可知他們更有不能了悟的更多。”尤氏笑道:“你倒好。纔是才子,這會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講起了悟來了。”惜春道:“我不了悟,我也捨不得入畫了。”尤氏道:“可知你是個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惜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狠心人,難得自了漢。’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爲什麼教你們帶累壞了我!”
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方纔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日。今見惜春又說這句,因按捺不住,因問惜春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丫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萬金的小姐,我們以後就不親近,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清淨。”尤氏也不答話,一徑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