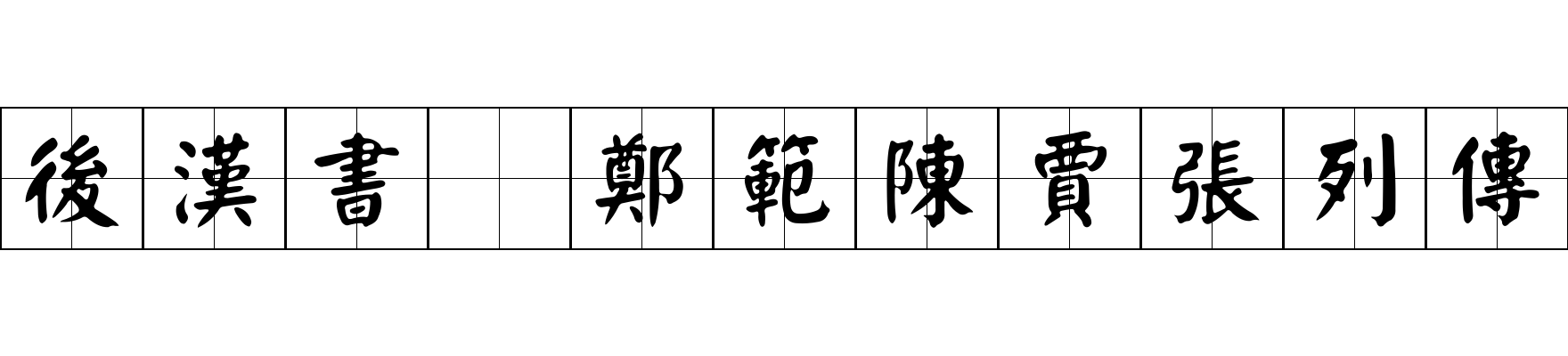後漢書-鄭範陳賈張列傳-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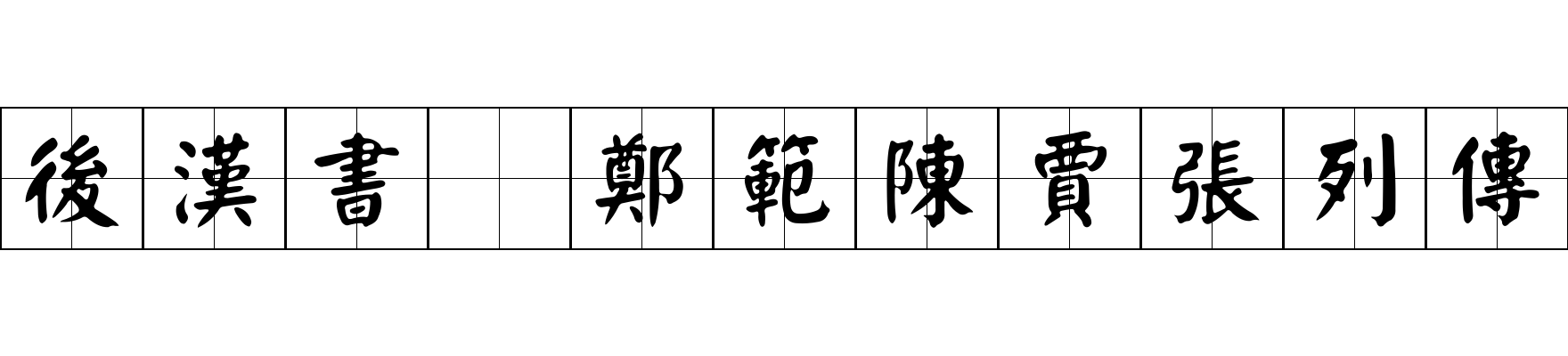
《後漢書》是一部由我國南朝劉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司馬彪續作),記載了從光武帝劉秀起至漢獻帝的195年曆史。
鄭興 子衆 範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曆》。
更始立,以司直李鬆行丞相事,先入長安,鬆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鹹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
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雲:‘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
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辨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
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冀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太中大夫。
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
《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 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亻及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鹹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子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書奏,多有所納。
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
九年,使監徵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徵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
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闢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鬆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鬆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
永平初,闢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侷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系廷尉,會赦歸家。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急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跡。
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複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廄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範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闢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鹹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雲不見,公雲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鶩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縣,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
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慚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範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猒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如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系,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CA75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範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余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竊見博士範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 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
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書奏,下其議,範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元以才高著名,闢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昊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鹹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帝從之,宣下其議。
李通罷,元后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
時,有神雀集宮殿宮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用《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
臣謹E74E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於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仇。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善,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B241。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
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鬱,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都字叔異,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
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
後就長水校尉樊B34A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鬆等。奉後爲潁川太守,鬆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初,霸以樊B34A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賴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發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 因遂家焉。 將作大匠翟D825等與諸儒門人追錄本行,諡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闢,舉賢良方正,不就。
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比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玩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
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裏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系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藉,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衝,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
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慚色。陵弟玄。
玄字處虛,沉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闢,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已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縣,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嘆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闢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強起,至輪氏,道病終。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氈幄。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