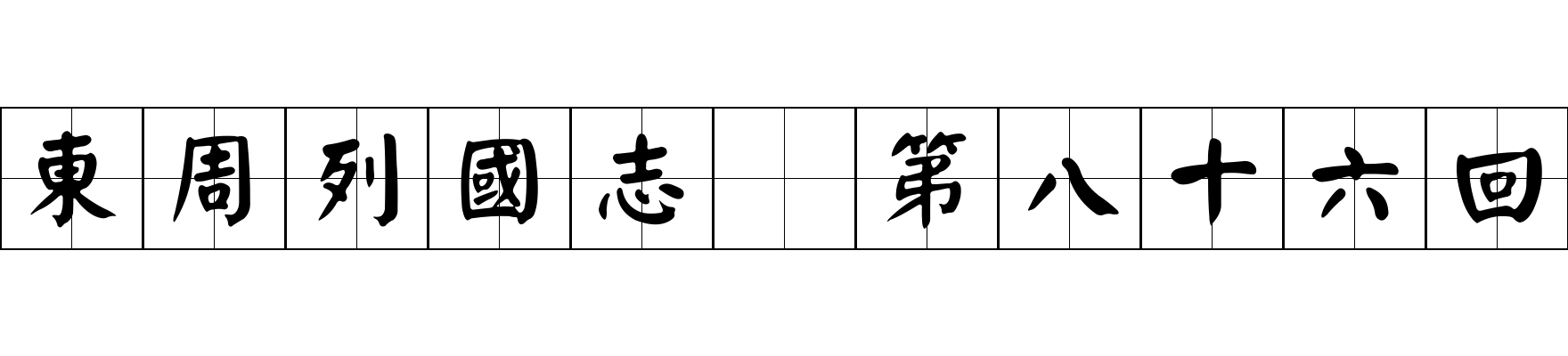東周列國志-第八十六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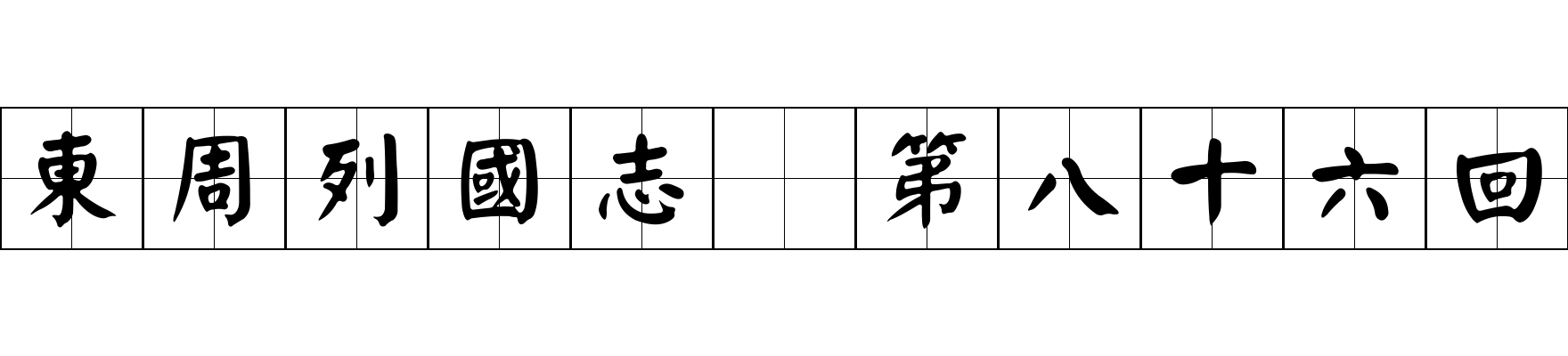
《東周列國志》是中國古代的一部歷史演義小說,作者是明末小說家馮夢龍。這部小說由古白話寫成,主要描寫了從西周宣王時期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五百多年的歷史。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關“列國”故事的白話本,明代嘉靖、隆慶時期,餘邵魚撰輯了一部《列國志傳》,明末馮夢龍依據史傳對《列國志傳》加以修改訂正,潤色加工,成爲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國志》。清代乾隆年間,蔡元放對此書又作了修改,定名爲《東周列國志》。
吳起殺妻求將 騶忌鼓琴取相
話說吳起,衛國人,少居里中,以擊劍無賴,爲母所責,起自齧其臂出血,與母誓曰:“起今辭母,遊學他方,不爲卿相,擁節旄,乘高車,不入衛城與母相見。”母泣而留之,起竟出北門不顧。
往魯國,受業於孔門高弟曾參,晝研夜誦,不辭辛苦。有齊國大夫田居至魯,嘉其好學,與之談論,淵淵不竭,乃以女妻之。起在曾參之門歲餘,參知其家中尚有老母,一日,問曰:“子游學六載,不歸省覲,人子之心安乎?”起對曰:“起曾有誓詞在前:‘不爲卿相,不入衛城。'”參曰:“他人可誓,母安可誓也?”由是心惡其人。
未幾,衛國有信至,言起母已死,起仰天三號,旋即收淚,誦讀如故。參怒曰:“吳起不奔母喪,忘本之人。夫水無本則竭,木無本則折,人而無本,能令終乎?起非吾徒矣!”命弟子絕之,不許相見。
起遂棄儒學兵法,三年學成,求仕於魯。魯相公儀休常與論兵,知其才能,言於穆公,任爲大夫,起祿入既豐,遂多買妾婢,以自娛樂。
時齊相國田和謀篡其國,恐魯與齊世姻,或討其罪,乃修艾陵之怨,興師伐魯,欲以威力脅而服之,魯相國公儀休進曰:“欲卻齊兵,非吳起不可。”穆公口雖答應,終不肯用,及聞齊師已拔成邑,休復請曰:“臣言吳起可用,君何不行?”穆公曰:“吾固知起有將才,然其所娶乃田宗之女,夫至愛莫如夫妻,能保無觀望之意乎?吾是以躊躇而不決也。”
公儀休出朝,吳起已先在相府候見。問曰:“齊寇已深,主公已得良將否?今日不是某誇口自薦,若用某爲將,必使齊兵隻輪不返。”公儀休曰:“吾言之再三,主公以子婚于田宗,以此持疑未決。”吳起曰:“欲釋主公之疑,此特易耳。”
乃歸家問其妻田氏曰:“人之所貴有妻者,何也?”田氏曰:“有外有內,家道始立,所貴有妻,以成家耳。”吳起曰:“夫位爲卿相,食祿萬鍾,功垂於竹帛,名留於千古,其成家也大矣,豈非婦之所望於夫者乎?”田氏曰:“然。”起曰:“吾有求於子,子當爲我成之。”田氏曰:“妾婦人,安得助君成其功名?”起曰:“今齊師伐魯,魯侯欲用我爲將,以我娶于田宗,疑而不用,誠得子之頭,以謁見魯侯,則魯侯之疑釋,而吾之功名可就矣!”田氏大驚,方欲開口答話,起拔劍一揮,田氏頭已落地。史臣有詩云:
一夜夫妻百夜恩,無辜忍使作冤魂? 母喪不顧人倫絕,妻子區區何足論!
於是以帛裹田氏頭,往見穆公,奏曰:“臣報國有志,而君以妻故見疑,臣今斬妻之頭,以明臣之爲魯不爲齊也!”穆公慘然不樂,曰:“將軍休矣!”少頃,公儀休入見,穆公謂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此殘忍之極,其心不可測也!”公儀休曰:“起不愛其妻,而愛功名,君若棄之不用,必反而爲齊矣!”穆公乃從休言,即拜吳起爲大將,使泄柳、申詳副之,率兵二萬,以拒齊師。
起受命之後,在軍中與士卒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見士卒裹糧負重,分而荷之;有卒病疽,起親爲調藥,以口吮其膿血。士卒感起之恩,如同父子,鹹摩拳擦掌,願爲一戰。
卻說田和引大將田忌、段朋長驅而入,直犯南鄙,聞吳起爲魯將,笑曰:“此田氏之婿,好色之徒,安知軍旅事耶,魯國合敗,故用此人也!”及兩軍對壘,不見吳起挑戰,陰使人覘其作爲。見起方與軍士中之最賤者,席地而坐,分羹同食。使者還報,田和笑曰:“將尊則士畏,士畏則戰力,起舉動如此,安能用衆,吾無慮矣!”
再遣愛將張醜,假稱願與講和,特至魯軍,探起戰守之意,起將精銳之士藏於後軍,悉以老弱見客,謬爲恭謹,延入禮待,醜曰:“軍中傳聞將軍殺妻求將,果有之乎?”起觳觫而對曰:“某雖不肖,曾受學於聖門,安敢爲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與軍旅之命適會其時,君之所聞,殆非其實。”醜曰:“將軍若不棄田宗之好,願與將軍結盟通和。”起曰:“某書生,豈敢與田氏戰乎,若獲結成,此乃某之至願也!”起留張醜於軍中,歡飲三日,方纔遣歸,絕不談及兵事。臨行再三致意,求其申好。
醜辭去,起即暗調兵將,分作三路,尾其後而行。
田和得張醜回報,以起兵既弱,又無戰志,全不掛意,忽然轅門外鼓聲大振,魯兵突然殺至,田和大驚,馬不及甲,車不及駕,軍中大亂,田忌引步軍出迎,段朋急令軍士整頓車乘接應,不提防泄柳、申詳二軍,分爲左右,一齊殺入,乘亂夾攻,齊軍大敗,殺得殭屍滿野,直追過平陸方回。
魯穆公大悅,進起上卿。
田和責張醜誤事之罪,醜曰:“某所見如此,豈知起之詐謀哉。”田和乃嘆曰:“起之用兵,孫武、穰苴之流也,若終爲魯用,齊必不安,吾欲遣一人至魯,暗與通和,各無相犯,子能去否?”醜曰:“願捨命一行,將功折罪。”田和乃購求美女二人,加以黃金千鎰,令張醜詐爲賈客攜至魯,私饋吳起,起貪財好色,見即受之,謂醜曰:“致意齊相國,使齊不侵魯,魯何敢加齊哉?”張醜既出魯城,故意泄其事於行人,遂沸沸揚揚,傳說吳起受賄通齊之事。穆公曰:“吾固知起心不可測也!”欲削起爵究罪。
起聞而懼,棄家逃奔魏國,主於翟璜之家。適文侯與璜謀及守西河之人,璜遂薦吳起可用,文侯召起見之,謂起曰:“聞將軍爲魯將有功,何以見辱敝邑?”起對曰:“魯侯聽信讒言,信任不終,故臣逃死於此。慕君侯折節下士,豪傑歸心,願執鞭馬前,倘蒙驅使,雖肝腦塗地,亦無所恨。”
文侯乃拜起爲西河守,起至西河,修城治池,練兵訓武,其愛恤士卒,一如爲魯將之時,築城以拒秦,名曰吳城。
時秦惠公薨,太子名出子嗣位。
惠公乃簡公之子,簡公乃靈公之季父,方靈公之薨,其子師隰年幼,羣臣乃奉簡公而立之,至是三傳,及於出子,而師隰年長,謂大臣曰:“國,吾父之國也,吾何罪而見廢?”大臣無辭以對,乃相與殺出子而立師隰,是爲獻公。吳起乘秦國多事之日,興兵襲秦,取河西五城,韓、趙皆來稱賀。
文侯以翟璜薦賢有功,欲拜爲相國,訪於李克。克曰:“不如魏成,”文侯點頭。
克出朝,翟璜迎而問曰:“聞主公欲卜相,取決於子,今已定乎,何人也?”克曰:“已定魏成。”翟璜忿然曰:“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君憂鄴,吾進西門豹;君憂西河,吾進吳起。吾何以不若魏成哉?”李克曰:“成所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非師即友。子所進者,君皆臣之。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以待賢士;子祿食皆以自贍。子安得比於魏成哉?”璜再拜曰:“鄙人失言,請侍門下爲弟子。”自此魏國將相得人,邊鄙安集,三晉之中,惟魏最強。
齊相國田和見魏之強,又文侯賢名重於天下,乃深結魏好,遂遷其君康公貸於海上,以一城給其食,餘皆自取。使人於魏文侯處,求其轉請於周,欲援三晉之例,列於諸侯。
周威烈王已崩,子安王名驕立,勢愈微弱,時乃安王之十三年,遂從文侯之請,賜田和爲齊侯,是爲田太公。自陳公子完奔齊,事齊桓公爲大夫,凡傳十世,至和而代齊有國,姜氏之祀遂絕,不在話下。
時三晉皆以擇相得人爲尚,於是相國之權最重。趙相公仲連,韓相俠累。
就中單說俠累微時,與濮陽人嚴仲子名遂,爲八拜之交。累貧而遂富,資其日用,復以千金助其遊費。俠累因此得達於韓,位至相國。
俠累既執政,頗著威重,門絕私謁。嚴遂至韓,謁累冀其引進,候月餘不得見。
遂自以家財賂君左右,得見烈侯,烈侯大喜,欲貴重之,俠累復於烈侯前言嚴遂之短,阻其進用。嚴遂聞之大恨,遂去韓,遍遊列國,欲求勇士刺殺俠累,以雪其恨。
行至齊國,見屠牛肆中,一人舉巨斧砍牛,斧下之處,筋骨立解,而全不費力,視其斧,可重三十餘斤,嚴遂異之,細看其人,身長八尺,環眼虯鬚,顴骨特聳,聲音不似齊人,遂邀與相見,問其姓名來歷,答曰:“某姓聶名政,魏人也,家在軹之深井裏,因賤性粗直,得罪鄉里,移老母及姊,避居此地,屠牛以供朝夕。”亦詢嚴遂姓字,遂告之,匆匆別去。
次早,嚴遂具衣冠往拜,邀至酒肆,具賓主之禮,酒至三酌,遂出黃金百鎰爲贈,政怪其厚,遂曰:“聞子有老母在堂,故私進不腆,代吾子爲一日之養耳。”
聶政曰:“仲子爲老母謀養,必有用政之處,若不明言,決不敢受!”嚴遂將俠累負恩之事,備細說知,今欲如此恁般,聶政曰:“昔專諸有言:‘老母在,此身未敢許人。'仲子別求勇士,某不敢虛尊賜。”遂曰:“某慕君之高義,願結兄弟之好,豈敢奪若養母之孝,而求遂其私哉。”聶政被強不過,只得受之,以其半嫁其姊罃,餘金日具肥甘奉母。
歲餘,老母病卒,嚴遂復往哭吊,代爲治喪,喪葬既畢。聶政曰:“今日之身,乃足下之身也,惟所用之,不復自惜!”仲子乃問報仇之策,欲爲具車騎壯士,政曰:“相國至貴,出入兵衛,衆盛無比,當以奇取,不可以力勝也。願得利匕首懷之,伺隙圖事,今日別仲子前行,更不相見,仲子亦勿問吾事。”
政至韓,宿於郊外,靜息三日,早起入城,值俠累自朝中出,高車駟馬,甲士執戈,前後擁衛,其行如飛,政尾至相府,累下車,復坐府決事,自大門至於堂階,皆有兵仗,政遙望堂上,累重席憑案而坐,左右持牒稟決者甚衆,俄頃,事畢將退,政乘其懈,口稱,”有急事告相國。”從門外攘臂直趨,甲士擋之者,皆縱橫顛躓,政搶至公座,抽匕首以刺俠累,累驚起,未及離席,中心而死,堂上大亂,共呼,”有賊!”閉門來擒聶政,政擊殺數人,度不能自脫,恐人識之,急以匕首自削其面,抉出雙眼,還自刺其喉而死。
早有人報知韓烈侯,烈侯問:“賊何人?”衆莫能識,乃暴其屍於市中,懸千金之賞,購人告首,欲得賊人姓名來歷,爲相國報仇,如此七日,行人往來如蟻,絕無識者,此事直傳至魏國軹邑,聶姊聞之,即痛哭曰:“必吾弟也!”便以素帛裹頭,竟至韓國,見政橫屍市上,撫而哭之,甚哀,市吏拘而問曰:“汝於死者何人也。”婦人曰:“死者爲吾弟聶政,妾乃其姊也,聶政居軹之深井裏,以勇聞,彼知刺相國罪重,恐累及賤妾,故抉目破面以自晦其名,妾奈何恤一身之死,忍使吾弟終泯沒於人世乎。”
市吏曰:“死者既是汝弟,必知作賊之故,何人主使,汝若明言,吾請於主上,貸汝一死。”
曰:“妾如愛死,不至此矣,吾弟不惜身軀,誅千乘之國相,代人報仇,妾不言其名,是沒吾弟之名也;妾復泄其故,是又沒吾弟之義也!”遂觸市中井亭石柱而死,市吏報知韓烈侯,烈侯嘆息,令收葬之。以韓山堅爲相國,代俠累之任。
烈侯傳子文侯,文侯傳哀侯。
韓山堅素與哀侯不睦,乘間弒哀侯,諸大臣共誅殺山堅,而立哀侯子若山,是爲懿侯。
懿侯子昭侯,用申不害爲相,不害精於刑名之學,國以大治,此是後話。
再說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斯病篤,召太子擊於中山。
趙聞魏太子離了中山,乃引兵襲而取之,自此魏與趙有隙。
太子擊歸,魏文侯已薨,乃主喪嗣位,是爲武侯,拜田文爲相國。
吳起自西河入朝,自以功大,滿望拜相,乃聞已相田文,忿然不悅,朝退,遇田文於門,迎而謂曰:“子知起之功乎。今日請與子論之。”田文拱手曰:“願聞。”
起曰:“將三軍之衆,使士卒聞鼓而忘死,爲國立功,子孰與起?”文曰:“不如。”
起曰:“治百官,親萬民,使府庫充實,子孰與起?”文曰:“不如。”
起又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犯,韓、趙賓服,子孰與起?”文又曰:“不如。”
起曰:“此三者,子皆出我之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某叨竊上位,誠然可愧,然今日新君嗣統,主少國疑,百姓不親,大臣未附,某特以先世勳舊,承乏肺腑,或者非論功之日也。”
吳起俯首沉思,良久曰:“子言亦是,然此位終當屬我。”有內侍聞二人論功之語,傳報武侯,武侯疑吳起有怨望之心,遂留起不遣,欲另擇人爲西河守。吳起懼見誅於武侯,出奔楚國。
楚悼王熊疑素聞吳起之才,一見即以相印授之。
起感恩無已,慨然以富國強兵自任,乃請於悼王曰:“楚國地方數千裏,帶甲百餘萬,固宜雄壓諸侯,世爲盟主。所以不能加於列國者,養兵之道失也。夫養兵之道,先阜其財,後用其力。今不急之官,佈滿朝署;疏遠之族,糜費公廩。而戰士僅食升斗之餘,欲使捐軀殉國,不亦難乎?大王誠聽臣計,汰冗官,斥疏族,盡儲廩祿,以待敢戰之士,如是而國威不振,則臣請伏妄言之誅!”
悼王從其計,羣臣多謂起言不可用,悼王不聽。於是使吳起詳定官制,凡削去冗官數百員,大臣子弟不得夤緣竊祿。又公族五世以上者,令自食其力,比於編氓;五世以下,酌其遠近,以次裁之。所省國賦數萬,選國中精銳之士,朝夕訓練,閱其材器,以上下其廩食,有加厚至數倍者,士卒莫不競勸,楚遂以兵強,雄視天下。三晉、齊、秦鹹畏之,終悼王之世,不敢加兵。
及悼王薨,未及殯斂,楚貴戚大臣子弟失祿者,乘喪作亂,欲殺吳起。起奔入宮寢,衆持弓矢追之,起知力不能敵,抱王屍而伏,衆攢箭射起,連王屍也中了數箭,起大叫曰:“某死不足惜,諸臣銜恨於王,僇及其屍,大逆不道,豈能逃楚國之法哉!”言畢而絕,衆聞吳起之言,懼而散走。
太子熊臧嗣位,是爲肅王。
月餘,追理射屍之罪,使其弟熊良夫率兵,收爲敵者次第誅之,凡滅七十餘家。髯翁有詩嘆雲:
滿望終身作大臣,殺妻叛母絕人倫。 誰知魯魏成流水,到底身軀喪楚人!
又有一詩,說吳起伏王屍以求報其仇,死尚有餘智也。詩云:
爲國忘身死不辭,巧將賊矢集王屍。 雖然王法應誅滅,不報公仇卻報私。
話分兩頭,卻說田和自爲齊侯,凡二年而薨,和傳子午,午傳子因齊,當因齊之立,乃周安王之二十三年也。因齊自恃國富兵強,見吳、越俱稱王,使命往來,俱用王號,不甘爲下,僭稱齊王,是爲齊威王。魏侯聞齊稱王,曰:“魏何以不如齊?”於是亦稱魏王,即孟子所見梁惠王也。
再說齊威王既立,日事酒色,聽音樂,不修國政。九年之間,韓、魏、魯、趙悉起兵來伐,邊將屢敗。
忽一日,有一士人,叩閽求見,自稱:“姓騶名忌,本國人,知琴,聞王好音,特來求見。”威王召而見之,賜之坐,使左右置幾,進琴於前,忌撫弦而不彈,威王問曰:“聞先生善琴,寡人願聞至音,今撫弦而不彈,豈琴不佳乎,抑有不足於寡人耶?”騶忌舍琴,正容而對曰:“臣所知者,琴理也,若夫絲桐之聲,樂工之事,臣雖知之,不足以辱王之聽也。”
威王曰:“琴理如何,可得聞乎?”
騶忌對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使歸於正。昔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其音以緩急爲清濁:濁者寬而不弛,君道也;清者廉而不亂,臣道也。一弦爲宮,次弦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文弦爲少宮,武弦爲少商,以合君臣之恩也。君臣相得,政令和諧,治國之道,不過如此。”
威王曰:“善哉,先生既知琴理,必審琴音,願先生試一彈之。”騶忌對曰:“臣以琴爲事,則審於爲琴;大王以國爲事,豈不審於爲國哉?今大王撫國而不治,何異臣之撫琴而不彈乎?臣撫琴而不彈,無以暢大王之意;大王撫國而不治,恐無以暢萬民之意也!”
威王愕然曰:“先生以琴諫寡人,寡人聞命矣!”遂留之右室。
明日,沐浴而召之,與之談論國事,騶忌勸威王節飲遠色,核名實,別忠佞,息民教戰,經營霸王之業。威王大悅,即拜騶忌爲相國。
時有辯士淳于髡,見騶忌唾手取相印,心中不服,率其徒往見騶忌。忌接之甚恭,髡有傲色,直入踞上坐,謂忌曰:“髡有愚志,願陳於相國之前,不識可否?”忌曰:“願聞。”
淳于髡曰:“子不離母,婦不離夫。”忌曰:“謹受教,不敢遠於君側。”
髡又曰:“棘木爲輪,塗以豬脂,至滑也;投於方孔則不能運轉。”忌曰:“謹受教,不敢不順人情。”
髡又曰:“弓幹雖膠,有時而解;衆流赴海,自然而合。”忌曰:“謹受教,不敢不親附於萬民。”
髡又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教,請選擇賢者,毋雜不肖於其間。”
髡又曰:“輻轂不較分寸,不能成車;琴瑟不較緩急,不能成律。”忌曰:“謹受教,請修法令而督奸吏。”
淳于髡默然,再拜而退。
既出門,其徒曰:“夫子始見相國,何其倨,今再拜而退,又何屈也?”淳于髡曰:“吾示以微言凡五,相國隨口而應,悉解吾意,此誠人才,吾所不及。”於是遊說之士,聞騶忌之名,無敢入齊者。
騶忌亦用淳于髡之言,盡心圖治,常訪問:“邑守中誰賢誰不肖?”同朝之人,無不極口稱阿大夫之賢,而貶即墨大夫者。忌述於威王,威王於不意中,時時問及左右,所對大略相同,乃陰使人往察二邑治狀,從實回報,因降旨召阿、即墨二守入朝。
即墨大夫先到,朝見威王,並無一言發放,左右皆驚訝,不解其故。未幾,阿邑大夫亦到,威王大集羣臣,欲行賞罰,左右私心揣度,都道:“阿大夫今番必有重賞,即墨大夫禍事到矣!”衆文武朝見事畢,威王召即墨大夫至前,謂曰:“自子之官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開闢,人民富饒,官無留事,東方以寧,繇子專意治邑,不肯媚吾左右,故蒙毀耳,子誠賢令。”乃加封萬家之邑,又召阿大夫謂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荒蕪,人民凍餒。昔日趙兵近境,子不往救,但以厚幣精金賄吾左右,以求美譽,守之不肖,無過於汝。”阿大夫頓首謝罪,願改過,威王不聽,呼力士使具鼎鑊。須臾,火猛湯沸,縛阿大夫投鼎中,復召左右平昔常譽阿大夫毀即墨者,凡數十人,責之曰:“汝在寡人左右,寡人以耳目寄汝,乃私受賄賂,顛倒是非,以欺寡人,有臣如此,要他何用。可俱就烹。”衆皆泣拜哀求,威王怒猶未息,擇其平日尤所親信者十餘人,次第烹之,衆皆股慄。有詩爲證:
權歸左右主人依,譭譽繇來倒是非。 誰似烹阿封即墨,竟將公道頌齊威。
於是選賢才改易郡守。使檀子篡守南城以拒楚,田肹守高唐以拒趙,黔夫守徐州以拒燕,種首爲司寇,田忌爲司馬,國內大治,諸侯畏服。威王以下邳封騶忌,曰:“成寡人之志者,吾子也。”號曰成侯,騶忌謝恩畢,復奏曰:“昔齊桓、晉文,五霸中爲最盛,所以然者,以尊周爲名也,今周室雖衰,九鼎猶在,大王何不如周,行朝覲之禮,因假王寵,以臨諸侯,桓、文之業,不足道矣!”威王曰:“寡人已僭號爲王,今以王朝王,可乎?”騶忌對曰:“夫稱王者,所以雄長乎諸侯,非所以壓天子也;若朝王之際,暫稱齊侯。天子必喜大王之謙德,而寵命有加矣!”
威王大悅,即命駕往成周,朝見天子,時周烈王之六年。王室微弱,諸侯久不行朝禮,獨有齊侯來朝,上下皆鼓舞相慶,烈王大搜寶藏爲贈,威王自周返齊,一路頌聲載道,皆稱其賢。
且說當時天下,大國凡七,齊、楚、魏、趙、韓、燕、秦。那七國地廣兵強,大略相等。餘國如越,雖則稱王,日就衰弱;至於宋、魯、衛、鄭,益不足道矣。
自齊威王稱霸,楚、魏、韓、趙、燕五國皆爲齊下,會聚之間,推爲盟主。惟秦僻在西戎,中國擯棄,不與通好。
秦獻公之世,上天雨金三日,周太史儋私嘆曰:“秦之地,周所分也,分五百餘歲當複合,有霸王之君出焉,以金德王天下。今雨金於秦,殆其瑞乎?”及獻公薨,子孝公代立,以不得列於中國爲恥,於是下令招賢,令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授以尊官,封之大邑。”不知有甚賢臣應募而來?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