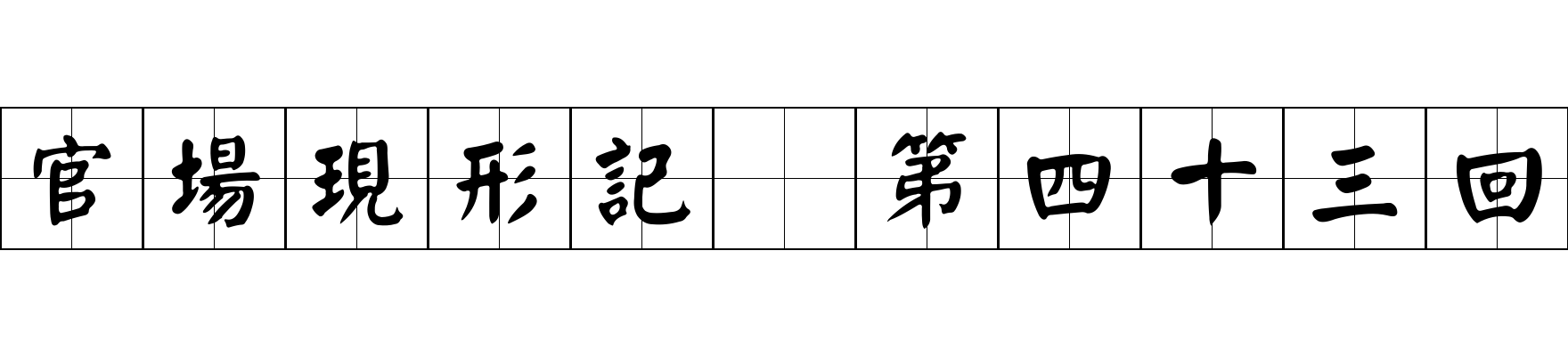官場現形記-第四十三回-相關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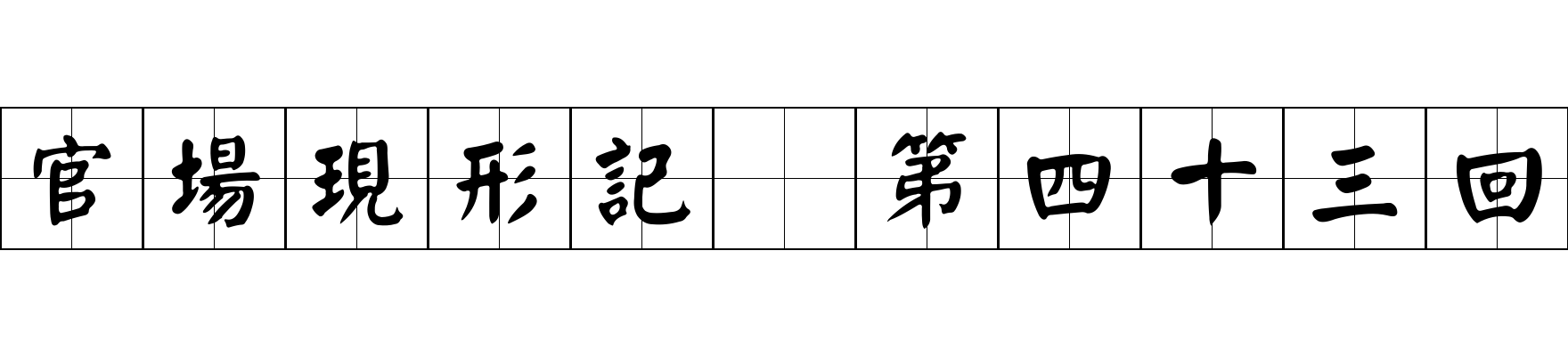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是晚清文學家李伯元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最早在陳所發行的《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共五編60回,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並取得社會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它由30多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聯綴起來,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雜小吏等,開創了近代小說批判現實的風氣。魯迅將《官場現形記》與其他三部小說並稱之爲譴責小說,是清朝晚期文學代表作品之一。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 一班齷齪堂構相承
話說小兔子去了三四天,賈制臺忽然接到蘄州知州一個夾單,說是“憲臺表老爺蕭某人趁了輪船路過卑境,停船的時候,上下搭客混雜不分,偶不小心,包裹裏的銀子被扒兒手悉數扒去,現在住在敝署,不能前進,請示辦理”等語。原來小兔子自從上了輪船,東張西望,並不照顧自己的行李,以致遇見扒手。當時齊巧解開包裹找衣服穿,一摸銀子沒有了,立刻吵着鬧着,要船上人替他捉賊。賊捉不到,就哭着要船上茶房賠他,一會又說要上岸去告狀。船上的人落得順水推船,趁着輪船還未離岸,馬上動手把他的行李送到岸上,由他去告狀。他問了問,曉得靠船地方是蘄州該管,忙坐了一輛小車子,奔到州里來告狀。這州官姓區,號奉仁,一聽是制臺的表弟,便也不敢怠慢,立刻請他到衙門裏來住,一面稟明制臺,請示辦法。夾單後面又說:“這銀子是在輪船上失去的。輪船自有洋人該管,卑職並無治外法權,還求大人詳察。”他的意思以爲着此一筆,這事便不與他相干,無非欲脫自己的干係。誰知制臺看了這兩句,心上不自在,便道:“不管他岸上水裏,總是他蘄州該管,少了東西就得問他要。我的親戚,他們尚且如此,別的小民更不用說了!”罷了,便下了一個札子,將蘄州區牧嚴行申飭,說他捕務廢弛,“限三天人贓並獲,逾限不獲,定行撤委”。區奉仁接到此信,無奈只得來同小兔子商量,私底下答應小兔子,凡是此番失去的銀子都歸他賠,額外又送了二十四兩銀子的程儀,又另外替他寫了船票,打發一個家人,兩個練勇,送他回籍。一面自己上省稟見制臺,面陳此事。
八座:漢,唐時稱尚書哈等爲八座。清代規定京官只能坐四人擡的轎子,但地方官督、撫有大典時可乘八人擡的轎,後代指督、撫爲八座。
這位區知州是晚上上了火就趕着過江的。到了省裏,恐怕制臺記掛表弟,立刻上院稟見。幸虧賈制臺是個起居無節的,三四更天一樣會客。巡捕、號房曉得他的脾氣,便也不敢回家,大家輪班在院上伺候。所以雖是三更半夜,轅門裏頭仍舊熱鬧得很。區奉仁走到官廳一看,已經有個人在那裏了。這個人歪在首縣一向坐慣的一張炕上,低着頭打盹,有人走過他的面前,他也不曾覺得。這裏官廳子共是三間廠間,只點了一支指頭細的蠟燭,照得滿屋三間仍是黑沉沉的,看得不十分清楚。區奉仁是久在外任,省城裏這些同寅素來隔膜,初時來時,見那人坐着不動,便也懶得上前招呼。此時正是十月天氣,忽然起了一陣北風,吹得門窗戶扇唏哩譁喇的響。蠟燭火被風一閃,早已蠟油直瀉下來,一支蠟燭便已剩得無幾了。區奉仁此時也覺得陰氣凜凜,寒毛直豎。正想叫管家取件衣服來穿,尚未開口,只見炕上那個打盹的人,忽然“啊唷”一聲,從炕上下來,站着伸了一個懶腰,仍就歪下,卻不知從那裏拖到一件又破又舊的一口鐘圍在身上,擁抱而臥;一雙腳露在外頭,卻是穿了一雙靴子。區奉仁看了甚是疑心,既不曉得他是個甚麼人:“倘若是個官,何以並無家人伺候,卻要在這裏睡覺?”一面尋思,一面看錶。他初進來的時候是十一點三刻,此時已經是三點一刻。
一口鐘:沒有袖子的外衣,也叫斗篷。
正在看錶,忽然聽見窗戶外面一班差人、轎伕蹲在那裏,嘴裏不住的唬哩唬哩的響,好像吃麪條子似的。區奉仁聽得清切,便想:“此時也不早了,肚裏也有些餓了,我何不叫他們也買一碗吃了,一來可以充飢,二來可以抵當寒氣。”主意打定,便想推出門去叫人。誰知外面風大得很,尖風削麪,猶如刀子割的一般。尚未開口,管家們早已瞧見,趕了進來,動問:“老爺有何使喚?”區奉仁連忙縮了回來,仍舊坐下,喘息稍定,便把買面喫的話說了。管家道:“三更半夜,那裏有賣面的。他們一般人是凍的在那裏唬哩噓哩的喘氣,並不是吃麪,老爺想是聽錯了。老爺要吃麪,等小的出去,到轅門外面去買了來。”區奉仁點點頭。管家自去買面。停了好半天,只買得一碗稀粥,說是天將四鼓,面是沒有的了。區奉仁只得罷休。
喫過了粥,登時身上有了熱氣,就問:“上頭爲什麼還不請見?”管家回道:“聽說同首府說話哩。首府從掌燈就進來,一直跑進簽押房!大人留着喫晚飯,談字,談畫,一直談到如今還沒有談完。江漢關道從白天兩點鐘到這裏,都沒有見着哩。這位大人只有同首府說得來,有些司、道都不如他。”區奉仁道:“首府本來同制臺是把兄弟。”管家道:“聽說現在又拜了門,拜制臺做教師,不認把兄弟了。通武昌省城,只有他可以進得內簽押房,別人只好在外頭老等。”區奉仁道:“照這樣子,可曉得他幾時才見?”管家道:“小的進來就問過號房,馬上就見亦說不定,十天半個月亦說不定,就此忘記了不見也說不定。”區奉仁道:“我是有缺的人,見他一面,把話說過了,我就要回去的。被他如此耽誤下來也好了!”管家道:“這話難說。不是爲此,怎麼這官廳子上一個個都怨聲載道呢?”
主僕二人正講得高興,忽見炕上圍着一口鐘睡覺的那個人一骨碌爬起,一手揉眼睛,一手拿一口鐘推在一邊,又拿兩手拱了一拱,說道:“老同寅,放肆了!你閣下才來了一霎工夫已經等的不耐煩,兄弟到這裏不差有一個月了!”區奉仁一聽這話,大爲錯愕,忙站起來,請教“貴姓、臺甫”。那人便亦起身相迎,回稱:“姓瞿,號耐庵。”區奉仁一聽這“瞿耐庵”三字很熟,想了一回,想不起來。
原來瞿耐庵自從到了興國州,前任因爲同他不對,前任帳房又因需索不遂,就把歷任移交的帳簿子一齊改了給他。譬如素來孝敬上司一百兩銀子的,他簿子上卻是改做一百元;應該一百元的,都改做五十元。無論瞿耐庵的太太如何精明,如何在行,見了這個簿子,總信以爲真,決不疑心是假造的。誰知這可上了當了:送一處碰一處,送兩處碰兩處,連他自己還不明白所以然,已經得罪的人不少了。你道前任帳房的心思可惡不可惡!
起初湍制臺的湖北,丫姑爺戴世昌腰把子挺得起,說得動話,瞿耐庵靠着他的虛火,有些上司曉得他的來歷,大衆看制臺分上,都不來同他計較,所以孝敬上司的數目就是少些,還不覺得。不料湍制臺一朝調離,丫姑爺尚且失勢,他這個假外孫婿更說不着了。賈制臺初署督篆,就有人說他話。起先賈制臺還看前任的面子,不肯拿他即時撤任。後來說他的壞話人多了,又把他在任上聽斷如何糊塗,太太如何要錢,一齊掀了出來。齊巧本府上省,賈制臺問到首府,首府又替他下了一副藥、因此纔拿他撤任。
撤任回省,接連上了三天轅門,制臺都沒有見他。後來因爲要甄別一票人,忽然想着了他,平空裏忽然傳見。瞿耐庵聞命之後,忙得什麼似的,也沒有坐轎子,就趕到制臺衙門裏來。來傳的人是十二點一刻到他公館,瞿耐庵沒有喫午飯,不到十二點三刻就趕到轅門,走進官廳,一直坐了老等。誰知左等也不見請,右等也不見請,想要回去,又不敢回去。肚裏餓得難過,只好買些點心充飢。看看天黑下來,找到一個素來認得的巡捕,託他請示。巡捕道:“他老人家的脾氣,你還不知道麼?誰敢上去替你回!他一天不見你,就得等一天;他十天不見你,就得等十天;他一個月不見你,就得等一個月。他什麼時候要見,你無論三更半夜,天明雞叫,你都得在這兒伺候着。倘若走了,不在這裏,他發起脾氣來,那可不是玩的!”原來這巡捕當初也因少拿了瞿耐庵的錢,心上亦很不舒服他,樂得拿話嚇他,叫他心上難過難過。瞿耐庵本來是個沒有志氣的,又加太太威風一倒,沒了仗腰的人,聽了巡捕的話,早嚇得魂不附體,只得諾諾連聲,退回官廳子上靜等。那知等到半夜,裏邊還沒有傳見。這一夜,竟是坐了一夜,一直未曾閤眼。
等到第二天天明,就在官廳子上洗臉,喫點心。停了一刻,上衙門的人都來了,管廳子上人都擠滿。等到制臺傳見了幾個,其餘統通散去,又只剩得他一個。仍舊不敢回家,只得又叫管家到公館裏搬了茶飯來喫。這日又等了一天,還沒請見。又去請教巡捕。巡捕生氣,說道:“你這人好麻煩!同你說過,大人的脾氣是不好打發的!既然來了,走不得!怎麼還是問不完?”瞿耐庵嚇的不敢出氣,仍回到官廳上。這夜不比昨夜了,因爲昨夜一夜未曾閤眼,身子疲倦得很,偶然往炕上躺躺,誰知一躺就躺着了。這一覺好睡,一直睡到第二天出太陽才醒。接着又有人來上院。他碰見熟人也就招呼,好像是特地穿了衣帽專門在官廳上陪客似的。一霎時各官散去,他仍舊從公館裏搬了茶飯來喫。只因其時天氣尚不十分寒冷,所以穿了一件袍套還熬得住。
如是者又過了幾天,一直不回公館。太太生了疑心,說:“老爺不要又是到漢口被什麼女人迷住了,所以不回來?”偷偷的自己過江探問。無意之中,又打聽到前次率領家人去打的那個人家,的確是老爺討的小老婆,那女人名喚愛珠,本是漢口窯子裏的人。當時不知道怎樣被夏口廳馬老爺一個鬼串,竟被他迷住了。後來瞿耐庵到任,很寄過幾百銀子給這女人。不過瞿耐庵懼內得很,一直不敢接他上任。那愛珠又是堂子裏出身,楊花水性。幸虧馬老爺顧朋友,說道:“倘喏照此胡鬧上去,終究不是個了局。”就寫了一封信給瞿耐庵,說愛珠如何不好,“恐怕將來爲盛名之累,已經替你打發了”瞿耐庵得信之後,無可如何,只索丟開這個念頭。如今這事全盤被太太訪聞,始而不禁大怒,既而曉得人已打發,方纔把氣平下。漢口找不到老爺,於是過江回省。怕家人說的話靠不住,又叫自己貼身老媽摸到制臺衙門州、縣官廳上瞧了一瞧,果然老爺一個人坐在那裏,方始放心。天天派了人送飯送衣服給老爺。過了幾天,又因天氣冷了,夜裏實實熬不住,被頭褥子無處安放,只送了一件一口鐘,又一條洋毯,以爲夜間禦寒之用。
閒話少敘。且說當時區奉仁拿他端詳了一回,方纔想起從前有人提過他是前任制臺的寄外孫婿。聞名不如見面,怎麼今天也會弄到這個樣子,便大略的問了一問。瞿耐庵是老實人,就一五一十的把從前如何得缺,後來如何撤任,回省上轅門,制臺如何不見,如今平空的傳見,及至來了,一等等了一個月不見傳見,以及巡捕又不准他走的話,詳述一遍。區奉仁聽了,一面替他嘆息,一面又自己擔心,不覺皺緊眉頭,說道:“吾兄在省候補,是個賦閒的人,有這閒工夫等他,兄弟是實缺人員,地方上有公事,怎麼夠耽擱得許久呢?”瞿耐庵道:“你要不來便罷,既然來了,少不得就要等他。我正苦沒有人作伴,如今好了,有了你老哥,我們空着無事談談,兄弟倒着實可以領教了。”區奉仁道:“不要取笑!他不見終究不是個事。兄弟這趟上省只帶了中毛衣服來,大毛的都沒帶,原想就好回任的。如今被你老哥這一說,兄弟還要派人回蘄州去拿衣服哩。”
瞿耐庵道:“今兒這個樣子大約是不會傳見的了。你把補褂脫去,也到這炕上來睡一回兒;就是不睡着,我們躺着談心。夜深了,天氣冷,兩個人睡在這炕上總比外面好些。我這裏還有一條洋毯,你拿去蓋蓋腳;我這裏有一口鐘,也可以無須這個了。”起先區奉仁還同他客氣,不肯上炕來睡。後來聽聽裏面杳無消息,夜靜天寒,窗戶又是破碎的,一陣陣的涼風吹了進來,實在有些熬不住了,瞿耐庵又催了三回,方纔上炕睡的。兩個人就拿了兩個炕枕作枕頭。
睡下之後,瞿耐庵又同他說:“不瞞老哥說:這三間屋裏,上面有幾根椽子,每根椽子裏有幾塊磚頭,地下有幾塊方磚,其中有幾塊整的,幾塊破的,兄弟肚子裏有一本帳,早把他記得清清楚楚了。”區奉仁聽他說得奇怪,忙問所以。瞿耐庵方同他說:“兄弟要見不得見,天天在這裏替他們看守老營。別人走了,單剩兄弟一個,空着沒有事做,又沒有人談天,我只好在這裏數磚頭了。”區奉仁聞言,甚爲嘆息。瞿耐庵又說:“我們睡一會罷。停刻天亮,又有人來上衙門,一耽誤又是半天哩。”卻好區奉仁也有點倦意,便亦朦朧睡去。次日起來,才穿好衣服,趕早上衙門的人已經來了。他倆是日又等了一天,仍未傳見。這夜又在官廳上蓋着洋毯睡了一夜。
到了第三天,區奉仁熬不住了。幸虧他是現任,平時制臺衙門裏照例規矩並沒有錯,人緣亦還好,便找着制臺的一個門口,化上一千兩銀子,託他疏通。那人拍胸脯說,各事都在他的身上。齊巧這天有人稟見,巡捕替他把手本一塊兒遞了上去,賈制臺叫“請”。進去的時候,惟恐大人見怪,兩手捏着一把汗。及至見了面,制臺挨排問話,問到他,只說得兩三句:第一句是“你幾時來的?”區奉仁恭恭敬敬回了聲“卑職前天就來了”。上頭又說:“長江一帶剪綹賊多得很啊,輪船到的時候,總得多派幾個人彈壓彈壓纔好。”區奉仁答應了兩聲“是”。制臺馬上端茶送客。區奉仁方纔把心放下。等到站了起來,又重新請一個安,說:“大人如無什麼吩咐,卑職稟辭,今天晚上就打算回去。”賈制臺點點頭道:“你趕緊回去罷。”說罷,把一干人送到宅門,一呵腰,制臺進去。
然後區奉仁又去上藩、臬兩司衙門。從司、道衙門裏下來,回到寓處,收拾行李。剛要起身,忽見執帖門上拿着手本上來回稱:“新選蘄州吏目隨太爺特來稟見。”區奉仁一看,手本上寫“藍翎五品頂戴、新選蘄州吏目隨鳳占”一行小字,便道:“我馬上就要出城趕過江的,那裏還有工夫會他。”執帖門道:“自從老爺一到這裏,纔去上制臺衙門,不曉得他怎樣打聽着的,當天就奔了來。老爺一直沒回家,他就一連跑了好幾趟。他說老爺是他親臨上司,應得天天到這裏來伺候的。”區奉仁聽他說話還恭順,便說了聲“請”。執帖門出去。
一霎時只見隨鳳占隨太爺戴着五品翎頂,外面一樣是補褂朝珠,因爲第一次見面,照例穿着蟒袍。未曾進門,先把馬蹄袖放了下來;一進門,只見他把兩隻手往後一癟,恭恭敬敬走到當中跪下,碰了三個頭,起來請了一個安。跟手從袖筒管裏拿履歷掏了出來,雙手奉上,又請了一個安。此番區奉仁見下屬不比見制臺了,大模大樣的,回禮起來,收了履歷。隨鳳占替他請安,他只拿只右手往前一豎,把腰呵了呵,就算已經還禮了。當下分賓坐下。區奉仁大約把履歷翻了一翻,因爲認得的字有限,也就不往下看了。翻完了履楞,便問:“老兄貴處是山東?”隨鳳占道:“卑職是安徽廬州府人。”區奉仁詫異道:“怎麼履歷上說是山東呢?”再翻出來一看,才知道他是山東振捐局捐的官,原來錯看到隔壁第二行去了。自覺沒趣,只得搭訕着問了幾句:“你是幾時來的?幾時去上任?”隨鳳占一一回答了。立刻端茶送客。也同制臺送下屬一樣,送了一半路,一呵腰進去了,隨鳳占又趕到城外,照例稟送,區奉仁自去回任不題。單說隨鳳占稟到了十幾天,未見藩臺掛牌飭赴新任,他心上發急。因爲同武昌府有些淵源,便天天到府裏稟見。頭一次首府還單請他進去,談了兩句,答應他吹噓,以後就隨着大衆站班見了。有天首府見了藩臺,順便替他求了一求。藩臺答應。首府回來,看見站班的那些佐雜當中,隨鳳占也在其內,進了宅門,就叫號房請隨太爺進來。號房傳話出去,隨鳳占馬上滿面春風,賽如臉上裝金的一樣,一手整帽子,一手提衣服,跟了號房進去。見面之後,首府無非拿藩臺應允的話述了一遍。隨鳳占請安,謝過栽培,首府見無甚說得,也只好照例送客。
等到隨鳳占出來之後,他那些同班的人接着,一齊趕上前來拿他圍住了,問他:“太尊傳見什麼事情?”隨鳳占得意洋洋的還不肯說真話,只說:‘有兩個差使,太尊叫我去,我不高興去。太尊叫我保舉幾個人,我一時肚皮裏沒有人,答應明天給他迴音。”大衆一聽首府有什麼差使,於是一齊攢聚過來,足足有二三十個,竟把隨鳳占圍在垓心。好在一班都是佐雜太爺,人到窮了志氣就沒有了,什麼怪像都做得出。其時正在隆冬天氣,有的穿件單外褂,有的竟其還是紗的,一個個都釘着黃線織的補子,有些黃線都已宕了下來,腳下的靴子多是尖頭上長了一對眼睛,有兩個穿着“抓地虎”,還算是好的咧。至於頭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絨的也有,都是破舊不堪,間或有一兩頂皮的,也是光板子,沒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裏,都一個個凍的紅眼睛,紅鼻子,還有些一把鬍子的人,眼淚鼻涕從鬍子上直掛下來,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裏揩抹。如今聽說首府叫隨鳳占保舉人,便認定了隨鳳占一定有什麼大來頭了,一齊圍住了他,請問“貴姓、臺甫”。
當中有一個稍些漂亮些的,親自走到大堂暖閣後面一看,瞥見有個萬民傘的傘架子在那裏,他就搬了出來,靠牆擺好,請他坐下談天。隨鳳占看看沒有板凳,難拂他的美意,只得同他坐下,也請教他的名姓。那人自稱姓申,號守堯,是個府經班子,二十四歲上就出來候補,今年六十八歲子。先捐了個典史,在河南等過幾年,分在衛輝府當差。有年派了個保甲差使,晚上帶了巡勇出門查夜。有一個喫酒醉的人,攔住當路罵人,被他碰見了。彼時少年氣盛,拉下來就五十板。等到打完了,那人才說:“我是監生。”捐了監的人,不革功名是打不得屁股的。當時無法,只得拿他開釋。誰知第二天,通城的監生老爺都來不答應他,說他擅責有功名的人,聲稱要到府裏去告他。他就此一嚇,卷卷行李逃走了。後來還是那個捱打的人恐怕鬧出來於自己面子不好看,私自出來求人家,勸大衆不要鬧了,這才罷休。後來本府也曉得了,明知他是畏罪而逃,樂得把差使委派別人。地方上少掉一個試用典史是不打緊的,倒也沒有人追究。他鬧了這個亂子,河南不能再去。齊巧他兄弟一輩子當中,當初有個捐巡檢的,後爲這人死了,他就頂了這巡檢名字,化幾個錢,捐免驗看,一直到湖北候補,正碰着官運享通,那年修理堤工案內,得了一個異常勞績,保舉免補本班,以府經補用。年代隔得遠了,他自己也常常拿從前的事情告訴別人,以鳴得意。還說什麼“你們不要瞧我不起,雖然是官卑職小,監生老爺都被我打過的!”人家聽慣了,都池他有些痰氣,沒有人去理會他。此時同隨鳳占拉攏上了,便嘻開了一張鬍子嘴,同隨鳳占一併排坐在傘架子上,扳談起來。隨鳳占難卻他這番美意,只得同他坐在一塊兒談天。
究竟佐雜太爺們眼眶子淺,見申守堯同隨鳳占如此親熱,以爲他二人一定又有什麼淵源,看來太尊所說的什麼差使,論不定就要被申某奪去了。於是有些不看風色的人,偏偏跟了他二人到暖閣後面,聽他二人講話。又有些醋心重的人,一旁咕嚕說道:“人家好,有門路,巴結得上紅差使。不要說起是一樁事情輪不到我們頭上,就是有十樁、八樁也早被後長的人搶了去了。我們何必在這裏礙人家的眼,還是走開,省得結一重怨。”又有些人說道:“我偏不服氣!我定要在這裏聽他們說些什麼。有什麼瞞人事情,要這樣鬼鬼祟祟的!”
一干人正在言三語四,刺刺不休,忽見斜刺裏走過一個少年,穿着一身半新的袍套,向一個老頭子深深一輯,道:“梅翁老伯,常遠不見了!小侄昨天回來就到公館裏請安,還是老伯母親自出來開門的,一定要小侄裏頭坐。小侄一問老伯不在家,看見老伯母還只穿了一件單襯子,頭也沒梳,正有那裏燒水煮飯,所以小侄也就出來了。今日湊巧老伯在這裏,正想同老伯談談。”又聽那老頭子道:“失迎得很!兄弟家裏也沒得個客坐,偶然有個客氣些的人來了,兄弟都是叫內人到門外街上頓一刻兒,好讓客人到房裏來,在牀上坐坐,連吃煙,連睡覺,連會客,都是這一張牀。老兄來了,兄弟不在家,褻瀆得很!”又聽那少年道:“老伯,小侄是自家人,說那裏話來!”又聽老頭子道:“老兄這趟差使,想還得意?”少年道:“小侄記着老伯的教訓,該同人家爭的地方,一點沒有放鬆。所以這趟差使雖苦,除用之外,也剩到八塊洋錢。”老頭子道:“你已經吃了虧了!到底你們年紀輕,是沒有什麼用頭的。”少年聽了不服氣,說道:“銀錢大事,再比小侄年紀輕的人,他也會丁是丁,卯是卯的;況且我們出來爲的是那一項,豈有不同人家要,白睜着眼喫人家虧的道理。”老頭子道:“你且不要不服氣。你走了幾個地方?”少年道:“我的札子一共是五處地方,走了半個多月才走完的。”老頭子說:“你又來!五個地方只剩得八塊洋錢,好算多?不信一處地方連着兩三塊錢都不要送。如今合算起來,每處只送得一塊六角錢。我們是老邁無能了,終年是輪不到一個紅點子。像你們年輕的人,差使到了手了又如此的辜負那差使,這才真正可惜哩。”少年道:“依你老伯怎麼樣?”老頭子道:“叫我至少一處三隻大洋,三五一十五塊錢總得剩的。”少年道:“人家送出來何嘗不是三塊、四塊,但是,自家也要用幾文。人家送了這筆洋錢來,力錢總得開銷人兩個。”老頭子把嘴一披,道:“你闊!你太爺要賞他們!他們跟慣州縣大老爺的人,那個腰裏不是裝飽的,就稀罕你這幾角洋錢!叫我是老老臉皮,來的人請他坐下,倒碗茶讓他喫,同他們謙恭些,是不犯本錢的。至於力錢,抹抹臉,我亦不同他們客氣了。人家見我如此待他,就是我拿出來,他亦不好意思收了。所以這筆錢我就樂得省下,自己亦好多用兩天,至於你說什麼零用,這卻是沒有底的,倘若要闊,一天有多少都用得完,但是貪圖舒服,也很可不必再出來當這個差使了。”
老頭子只管絮絮叨叨不住,少年聽了甚不耐煩。齊巧隨鳳占同申守堯在暖閣後面談了一回也走了出來。申守堯是認得那兩個人的,便問少年道:“你同梅翁談些什麼?”少年正待開口,卻被老頭子搶着說了一遍,無非是怪少年不知甘苦,不會弄錢的一派話。少年聽了不服氣,又同他爭論。申守堯便從中解勸道:“這話怪不得梅翁要說。你老兄派的幾處地方總還在上中字號裏頭。他們現任大老爺。一年兩三萬往腰裏拿,我們面上,他就是多應酬幾文,也不過水牛身上拔一根毛。所以兄弟也是出差每到一處,等他們把照例的送了出來,我一定要客氣,同他們推上兩推。並不說嫌少不收,我興說:‘彼此至好,這個斷斷乎不敢當的。不過在省城裏候補了多少年,光景實在不好,現在情願寫借票,商借幾文,’如此說法,他們總得加你幾文。有些客氣的,借的數目比送的數目還多。”少年道:“開口問人家借,借多少呢?”申守堯道:“這也沒有一定。總而言之:開出口去伸出手去,不會落空就是了。”少年道:“到底這借票還寫不寫呢?”申守堯道:“你這人又呆了,錢既到手,抹抹臉皮,還有什麼筆據給人家。倘若一處處都寫起來,要是一年出上三趟差,至少也寫得二十來張借票,這筆帳今輩子還得清嗎?不過是一句好看話罷了。況且幾塊錢的小事,就是寫票據,人家也不肯接手的,倒不如大大方方說聲‘多謝’,彼此了事。”
三個人正說得高興,不提防隨鳳占站在旁邊一齊聽得明明白白,便插口說道:“守翁的話呢,固然不錯。然而也要鑑貌辨色,隨風駛船。這當中並沒有什麼一定的。”衆人見他一旁插口,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不覺都楞在那裏。申守堯便替他拉扯,朝着一老一少說:“這位是新選蘄州右堂,姓隨,官印叫鳳占。宦途得意得很,不日就要到任的。而且是老成練達,真要算我們佐雜班中出色人員了!”一老一少聽了,連忙作揖,極道仰慕之忱。申守堯又替二人通報姓名,指着年老的道:“這位姓秦,號梅士,同兄弟同班,都是府經。”又指年少的道:“這位學槐兄,今年秋天才驗看。同太尊第二位少奶奶孃家沾一點親,極蒙太尊照拂,到省不到半年,已經委過好幾個差使了。”隨鳳占亦連稱“久仰”。又道:“恰恰聽見諸公高論,甚是佩服!”秦梅士道:“見笑得很!像你老兄,指日就要到任的,比起我們這些終年聽鼓的到底兩樣。”隨鳳占道:“豈敢,豈敢!不過兄弟自從出來做官,一直是捐了花樣,補的實缺,從沒有在省城裏候補過一天。不過這裏頭的經濟,從前常常聽見先君提起,所以其中奧妙也還曉得一二。”衆人忙問:“老伯大人從前一向那裏得意?”隨鳳占道:“兄弟家裏,自從先祖就在山東做官。先祖見背之後,君也就驗看到省,一直是在山左的,等到兄弟,卻是一直選了出來,僥倖沒有受過這苦,雖然都是佐班,兄弟家裏也總算得三代做官了。”衆人道:“有你老哥這般大才,真要算得犁牛之子,跨竈之兒了。但是老伯從前是怎麼一個訣竅,可否見示一二?”申守堯道:“你們不要吵,且聽他說。老成人的見解一定是不同的。”
山左:山東舊時的別稱,因在太行山之左(東)而得名。
“犁牛之子”:《論語·雍也》:“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仲弓之父賤且惡,而仲弓是個人才,孔子的話是比喻父惡子賢。
“跨竈之兒”:比喻兒子勝過父親。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叫竈門。良馬的後蹄印反在前蹄印之前,叫跨竈。
隨鳳占道:“先君從前在山東聽鼓的時候,有年奉首府的札子,叫老人家到各屬去查一件什麼事情。先君到了第二縣,我還記得明明白白的,是長清縣。這長清在山東省裏也算一個上中缺,這位縣大爺又同先君稍爲有些淵源。到了長清,見面之後,他就留先君到衙門裏去住。先君一想,住店總得錢,有得省樂得省,就把鋪蓋往衙門裏一搬。橫豎衙門裏空房子多得很。先君住的那間屋子就在帳房的緊隔壁。當時住了下來,本官又打發門上來招呼,說:‘請太爺同帳房一塊兒喫飯。’衙門裏大廚房的菜是不能進嘴的,帳房師爺要好,又特地添了兩樣菜,先君喫着倒也很舒服。誰知住了一夜,第二天本官就下鄉相驗去了,離城一百多里路,來回總得三四天。臨走的時候還同先君說:“老兄不妨在這裏多盤桓幾天。倘若要緊動身。一切我已交代過帳房了。’先君以爲他已經交代過帳房,總不會錯的。第三天,先君覺着住在那兒白擾人家沒有味兒,就同帳房商量,說要就走的話。帳房答應了。先君先回到屋裏收拾行李。停了一會,帳房就叫人送過兩吊京錢來,說是太爺的差費。先君此來本想他多送兩個的,等到兩吊錢一送出來,氣的話都說不出!”申守堯道:“兩吊錢還比兩塊錢多些,現在一塊洋錢只換得八百有零。”隨鳳占道:“呀呀呼!我的太爺!北邊用的小錢,五百錢算一吊,一個算兩個,兩中只有一千文,合起洋錢來還不到一元三角。”申守堯道:“那亦太少了。”隨鳳占道:“就是這句話了。所以當時先君見了,着實動氣,就同送錢來的人說:‘我同你家大老爺的交情並不在錢上頭,這個斷斷乎不好收的。’那人聽了先君的話,先還不肯拿回去,後來見先君執定不收纔拿了的。帳房就在隔壁,是聽得見的。那人過去,把先君的話述了一遍。只聽得帳房半天不說話,歇了一回,才說道:“兩吊不肯,只好再加一吊。這錢又不是我的,我也不便拿東家的錢亂做好人。’先君一聽隔壁的話,知道不妙。等到第二趟送來,這時候頂爲難:倘若是不推,明明是同他爭這一吊錢,面子上不好看,無奈,只得略爲推了一推。那送來的人自然還不肯拿回去。先君也就自己轉圜,說道:‘論理呢,這個錢我是不好收的。但是你們大老爺又不在家,我倘若一定不收,又叫你們師老爺爲難,我只好留在這裏。師老爺前,先替我道謝罷。’諸公,你們想,這時候倘若先君再不收他的,他們索性拿了回去,老實不再送來,你奈何他?你奈何他?所以這些地方全虧看得亮,好推便推,不好推只得留下。這就叫做見風駛船,鑑貌辨色。這些話是先君常常教導兄弟的。諸公以爲何如?”大家聽了,一齊點頭稱“妙”,說:“老伯大人的議論,真是我們佐班中的玉律金科!”
正說得高興,忽見一個女老媽,身上穿的又破又爛,向申守堯說道:“老爺的事情完了沒有?衣裳脫下來交代給我,我好替你拿回去。家裏今天還沒米下鍋,太太叫我去噹噹,我要回去子。”申守堯不聽則已,聽了之時,怪這老媽不會說話,伸手一個巴掌,打的這老媽一個趔趄,站腳不穩,躺下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